第二天,监狱门前不大的空地上挤满了帮教家属,许多人不明程序、不知地点地乱撞。领着贺明母亲和小玲登记完,把他们安排到同事办公室,我便想先进监区。临走,老人把我拉到一边,面有难色地说:“指导员……”
“您叫我小赵。”我苦笑着纠正。
“赵指导员,贺明这个娃来的信我都看了,几次提到你,看来是挺……挺信你的。你能不能……先去替我劝劝他,告诉他见着小玲别让人家难堪。这个娃死犟着咧……”
我不懂地看她,老人眼圈一红,堆满皱纹的眼角淌出泪水,“明娃出事以后,小玲爹妈就再不让她登我们家门,说反正也没扯证没办事,算不得正式夫妻。前些年玲还小不敢违拗她家老人,也给明娃写了绝交信,没想到,这两年姑娘大了,背着爹妈总上我那儿做这做那。可明娃就是心眼儿小,跟人家记了仇,从不回信,这趟就是小玲死活拉我来的……”说着,她望了望坐在办公室里有些拘束的小玲,叹了口气,“你就帮我说说他,啊?”
“哦”,我不知所以地答应着,说了太多的话,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不清。
贺明早早站在教学楼门口,簇新洁净的衣服显示了隆重的等待,平日唇边偶有泛起的胡须也剃得干干净净,露出令我心动的青色,坚毅而性感。
忽然想起前天给他留下剃须刀,他把玩着问违规了吧,这可是违禁品!我瞪他一眼,知道违禁就注意藏好了。他淘气地皱着眉追问藏哪儿藏哪儿啊,还顺手指指自己的裤裆,你看这儿行吗?我抬手就是一下,碰到了软软的东西,红着脸说放到库房里吧,你不也有钥匙?他眼珠咕碌转了一圈说我可不敢去,到那地方容易想入非非,你又不在……一切都刚刚发生,那么真实,恍若眼前。难道就真的要对这些时时在梦中笑醒的温馨挥手告别?
他就那样干干净净地站在阳光里望着我笑,一如过去每个普普通通的早晨。晨曦中脸庞与胳膊上的汗毛仿佛清晰可见,让人想起掠过肌肤时陡然而生的酥痒,鼻腔里忽然就充溢了酸酸的液体,眼前跳跃着各种光线的折射和反射,宛若彩虹斑澜。
“昨天我妈没训你吧”贺明颠着脚在我身边晃,“没办法呃,她对我都那样,不过,她是软心肠,和你一样。”
我没像往常那样跟他逗嘴,低头径直走进活动室,过一会儿他们一家人就要在这儿吃饭,现在应该摆上了水果、花生等等,这些还真是监狱准备的。
贺明一开始还跟在我身后,慢慢看见我毫无表情的神色,就落在后面,一脸疑惑和茫然。
我无法追问无法责备也无法开口,她母亲说得很清楚,贺明什么都不知道,怪不得他。可这就能让我们对小玲视如空气吗?
实在不忍心看他无辜和委屈,我扭过脸笑笑,“去准备准备吧,马上就来了。”我真的做不到和贺明板脸,就像他说的,怎么可能跟我生气一样。见我又笑了,他用力打了个响指,一溜烟跑回号房。
教育科的民警分别领着家属一个监区一监区地护送,最后才来到教学楼。本来还有另外一户,临时告知来不了了。
贺明站在楼外几米处,我站在高高的楼门口,或许还有很多犯人站在窗前眺望,想起自己遥远的亲人。
几个人影还在足够远的地方,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贺明掩饰不住兴奋地扭头朝我眨眨眼,颠起脚尖向那边张望,其实大院里非常平整,所谓颠脚并不一定能真正使视野更开阔。
人越走越近,我死死盯住了贺明的背影还有被阳光拉长的影子。
蓦地,贺明转过身,张张嘴,眼神透露出惊异、气恼和不确定。就当他再次转回去看时,母亲和小玲已经到了跟前。
不时有人从号房探出头来张望,我能理解这种长久与外界隔绝后对新鲜事物的浓厚新奇,其实这无关来人的身份、性别、外貌,即使是高墙外那株在春意里萌发新芽的钻天杨,那只飞过电网、掠过监狱上空的白鸽,一样能引发他们无限的瑕想与慨叹,我想那是对自由渴望的表达。
贺明三人跟在我身后走进活动室,老祁和另外早已安排好的两个服务犯一脸热情地鼓掌欢迎。毕竟,远来都是客,这也算中国人骨子里难以彻底消除的待人之道。即使身处这样一个遍布冷酷的地方,在这样特殊的时候,那几声鼓掌也不能完全算作虚伪吧?
贺明母亲的眼睛一直湿润着,双手不停在他身上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从来都很坚强的贺明低着头,大概不想让母亲看到控制不住的眼泪,浓浓的亲情洋溢在整个活动室,我、老祁,包括那两个犯人也不约而同地红了眼圈。
老人客气地让我们一同来坐。经历过很多这样场面的老祁侃侃而谈着她们的进监帮教会对贺明的改造产生多大多大影响,似乎放弃这次机会,贺明注定会再次走向无底的深渊。这会儿,我倒不认为他在故意作秀,被所谓党的教育改造方针洗脑的结果这是如此。也许在他们潜意识里,真的认为亲情感化一定能达到那些狗屁理论所阐述的高度……虚无缥缈的高度。
贺明眼睛一直没有看身旁的小玲,似乎在他身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场”,面对母亲的嘘寒问暖与侧脸的冷若冰霜分别过于鲜明,小玲僵硬着表情,不时看看对面的母亲,显得既孤独又无助。
我同老祁与贺明母亲打了声招呼,说你们慢慢聊。目光与贺明相对,感觉他又张张嘴想说什么,通红的眼睛里闪动着急于解释却无法开口,渴望我留下又担心尴尬的复杂情绪。我毫无表情地让目光在他身上飘过,坚决地转身离开。我所拥有的情商和智慧不足以应对这一切,无论出现怎样的情景都会刺痛本不坚强的心。
独自坐在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快发干的香烟放在指尖把玩。想起贺明一次不经意地说起抽烟的害处劝我少抽,我问在这个事上是我随了你还是你随了我?他拿起烟盒无比沉痛地说你要是不想戒的话也行,我就比你多抽十倍,不信你不心疼!
我怎么能不心疼?可现在,这心疼会不会再没了投射与给予的地方,或者,在接纳时他会多几分顾虑、内疚和左顾右盼?
火苗腾空而起,烟雾便袅袅扩散开来。才两个星期没抽,我竟已不适应那呛人的味道,剧烈咳嗽起来。眼泪,憋了一夜的眼泪借机汹涌而出,不由分说、不能控制,我伸手捂住了脸。
忽然楼道里传来高高低低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监狱为了维持帮教秩序,特别规定这一天其他犯人必须待在号房里组织学习,我赶忙抹了把脸走出办公室。
那是活动室传来贺明母亲压抑的抽泣声。心里一惊,急步跑过去。老祁和两个犯人站在一旁,正无可奈何看着同样激动的三个人。贺明熟悉的倔倔的表情望向窗外,老人不断拍打他的肩背,泣不成声,小玲则坐在一边偷偷抹眼泪。
见我进来,老祁粗着嗓子喊:“贺明你犟什么犟?别忘了这儿还是监狱,想由着性子等出去再说!”
“那……那我不帮教了!”贺明梗着脖子起身说道,脸涨得通红,“妈,你……回吧。”说完,咚咚往外跨步。
我垂手站在门口,脑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想。当他经过,猛地扯住胳膊,用力推了一把,他便趔趄着退后几步,几欲倒地,等站稳了,贺明呼地转过身面对窗户直直地立着一动不动。
老祁用手指头点了点贺明的背影,摇摇头气乎乎地离开活动室。这怪不得他,本来应该是一家人团聚,他可以好好享受一下管理者和主宰者的良好感觉,这种机会对他来讲也许不常有。我让那两个犯人也各自回去,屋内只剩下细细碎碎的抽泣声。
走到贺明面前,我与他直直对望着。无法言尽那双不再清澈的双眸里究竟包含了多少思绪,多少来自于我又回馈于我?只是,我们现在还无瑕顾及彼此之间存在的小小疑虑,似乎与那相比,眼前的一切更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我拍拍他,算是对刚才那一推的歉意。借转身的机会,在背后轻轻抚摸了几遍。记得他说这是他的“命门”,什么时候不舒服了,只要我上下左右来几下,一切都会OK。
“你这个娃……以为这几年监狱把你教好了,没想到,还这么不懂事理。这两年小玲容易吗?顶着爹的眼娘的训不就是为了和你过到一起?你怎么就……”老人伤心地絮叨着。
“娘,你别说了……”小玲掩面控制不住地哭出声来。我刚想说几句劝慰的话,忽然,她扑通竟跪在了贺明面前。
脑子嗡地一声,我几乎不相信看到的场景。是怎样刻骨的感情经历才会让她做出如此的动作来,如此忘掉外人的目光,内心的尊严和受过的委屈,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寻求贺明的谅解?
贺明呆了片刻,伸出手想搀起小玲,小玲猛地扑到他怀里,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再也不肯松手。
隔着小玲,对面的贺明不知所措地张开手臂,似乎也被突如其来的情景惊了一跳,手在空中几起几落,终于还是放在了因哽咽而不时起伏的小玲的背上。从我这边看过去,两人仿佛刚刚经历悲欢、生死、离合一样紧紧贴在一起,如同许多电影结局想要表达的情节:不堪的过往不必解释,只愿这样相拥到老。
一瞬间,心像被人狠狠地攥了一把,失血般只剩下空空的跳动。面对,刚才还涌上心间的所谓共同面对的念头,被眼前的一切击得粉碎。没有人要和我一起面对什么。只不过,是我要独自面对疑问、彷徨、选择。还有,那些未必需要有我参与的决断。
低下头,我长长舒了口气,向抹着眼泪转悲为喜的贺明母亲笑笑,走了出去。
正值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地面上,远处楼房、花池、绿地隔着蒸腾起的气流,摇移不定、变形怪异。眯上眼睛,我走进烈日,走出教学楼。
从没有一种简单的善恶因果为结局提供依据,也没有鲜明的是非判断承转千头万绪的情节。在不可预知的未来里,我失去了抉择的能力,只有听凭而没有争取,只有顺从而难以挣扎。
傍晚时分,接到贺明母亲打来电话,说她们已经准备上车返家,反复谢谢一天来我的照顾。叮咛我再好好教育教育贺明,别再死倔死倔的。最后她还留了小玲家的电话,希望有什么事及早通知她们。
我茫然地盯着那串数字,幻想离开后三人一起吃饭的情形。贺明说我心肠软,其实我更了解他。那惊天跪倒,那忘情一抱,应该早就软化了他或许并不那么固执的成见。即使过去的爱还未苏醒,他也不会再让两个女人为难的。
星期一,我借故在同事办公室里聊了很久,估摸着齐林已经开始训练,才无精打采地走进监区。老祁还在为昨天贺明的鲁莽耿耿于怀,说临走时这家伙居然只跟老太太交待来交待去,把媳妇撂在一边,真不知道咋想的。我试探地问你觉得怎么回事?他皱了半天眉毛说,听那意思好像贺明觉得媳妇对他不住,可后来又说跟她没什么关系,搞不懂。
愣愣地站在窗前,望着远处发呆,我没注意老祁后面跟了句什么追问的话语。
趁着贺明还没回来,我找个借口又先出了监区。我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躲避什么,总觉得有些代价应该付出,否则那圣洁的亲情与感动会不时惊扰宁静的梦,会每每让我不得安宁。冥冥中,我像是在找寻一个说服自己继续下去的理由,哪怕只是屈从于情怀的召唤、折服于爱的吸引、或者是对经受折磨的补偿。我想,如果答案来得太快,不是缘于轻率就是经不起内心的拷问。
一连三天,我都晚进早出,避免与贺明碰面。老祁奇怪地问最近很忙吗?我支吾着点头,心里升起一声长叹。是忙吧?忙着与煎熬、与本性、与来自咫尺的诱惑搏杀,经常身心俱疲、无力喘息。我就像一只自我束缚的蚕蛹,在一圈一圈的缠绕中欲动不能,几乎窒息。在等待与折磨中,为自己找个理由的初衷越来越似是而非,取而代之的是无法平复的思念,对那双有力的臂膀,浑厚的胸膛,迷人气息的思念,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堕落,算不算精神对身体的认输。
这天老祁去了训练场,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胡乱勾画,半天才发现整张纸竟写满了贺明两个字。苦笑着站起身,刚想伸开两臂打个哈欠,视野里竟出现了熟悉的身影,脚步匆匆低着头往教学楼这边奔过来。
我不知道该摆出一种什么样的姿势来迎接这次不同寻常的见面,至少要给他一个明确的信息。可就在我来回转身的时候,贺明已通地一声推开了门。
他跑得满头是汗,胸口急促起伏,与我目光相对,他一手扶着门框,竟忘记了关上。
只一眼,就明白所谓要追问的理由和答案其实都敌不过活生生的自上而下、从里到外散发着独特气息的这个男人。我转过脸背对他,怕这些天积蓄的欲望破茧而出,在我看来那还是只未成熟的飞蛾,有些丑陋见不得天日。
“昨天、前天我都来……报到了,可……你不在。”贺明站在门口低低地说。
眼泪迅速就聚满了眼眶,我努力噙住不让它们掉下来。为什么要说这些,这些让几天来堆积起的疑问、委屈甚至怨尤瞬间土崩瓦解的话?
他走近柔声道,“就算要骂,也得给我个站到你面前的机会吧?”他牵住了我背在身后的手,厚厚的老茧掠过掌心,温暖、有力一如从前。转过身,我无法抑制地任眼泪在他面前跌落。
相思太紧。
所有需要澄清的过往,需要追问的答案都放到一边,让我们先告诉对方,控制不了的、阻挡不了的对彼此的深切渴望!我以为事隔三天后的相见,会尴尬会难堪至少,会有一丝的犹豫,没想到,炙烤融化的岩浆酝酿得愈久,喷薄的力量愈势不可挡。
那些答案真的就被放到了一边,轻轻地、默契地、无奈地。
贺明说,对母亲他已讲清楚,几年来倔强、不肯低头的相同个性在本应水乳交融的母子间产生了不小的隔阂,现在他也长大,希望母亲不要再逼问这件事情。
对小玲他表示得很明白,虽然出事与小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才弄清楚贺明当初就是为了替小珍哥哥出头,才动手误伤了那个村霸),但她没必要因此内疚一辈子;至于两人之间的恩怨,既然已曾那么绝决地彼此伤害过、抛弃过,就不要再试图忽略、弥合不可能消除的裂痕。说这话时,他用力咬了咬牙,腮边肌肉随之一紧一紧,似乎要坚定某个念头般,脸上浮现出坚毅的表情。
我根本不可能再去自私地询问我们怎么办,或者要他抽丝剥茧地解释与小玲之间的恩怨、伤害、负欠究竟是怎样难以厘清。每个人都有历史都有故事,这个道理我懂。
他板过我扭到一边的脸,仿佛恢复了熟悉的调皮,“怎么,不准备骂我了?”
我终于知道沦陷于一个人的微笑当中是多么悲哀。那意味着不管你正经历怎样的伤痛,面对多少折磨,只要他微微翘起嘴唇,眯起眼睛,你就会忘掉所有,乖乖地跟随他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义无反顾。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真有什么在我们周围发生过。那些本来沉重得无以复加,紧急得火烧火燎,逼迫得动弹不得,甚至狂澜既倒,大厦将倾的困扰,怎么就忽地没了踪影,只感到和他在一起的安宁、静心?我们称之为爱的东西,莫非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失去,对自我;一种无端的信任,对对方?
我们不约而同地避免再谈及那次帮教。未来,即使没有他母亲与小玲参与的未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路坦途?我不敢妄自揣测。我甚至违心而宽慰地想:《射雕》里蓉儿送靖哥哥回蒙古迎娶华筝公主的一路上,不是也说过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的话。或许,我们能有类似“柳暗花明”的结局也未可知。那么,不如对酒当歌,不如衣袂飘舞,何必去管身后巨浪滔天?
接到巡演的命令,已经是两个星期后的事情。这期间,贺明往家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厚厚地装在信封里让我帮着寄了。以前我从来不看他寄出的信件,监狱规定的信件审查关过于死板,让不少干部平添了窥人隐私的“爱好”,甚至把这当成聊天的谈资,坏了形象,失之严肃。可这次,我却鬼使神差地在投寄的一刹那摊开纸简略扫了一眼。
贺明非常认真地和父母探讨了出狱后的生活,说如果回家的话难免多一分困扰,无论是来自亲人路人还是敌人,他托父母一定要劝说小玲放弃等他的念头,别再耽误了人家。整个信唠唠叨叨一大堆,仿佛怕父母不理解似的,将道理切开了揉碎了再和到一起反复说,与他平日里简洁的作风相去甚远。
将信塞进信筒,我虔诚地合什祷告,以至于旁边寄信的人奇怪地瞅我笑了笑。
离巡演还有一个星期。于是拖长训练时间,于是加大训练强度,于是贴出了“塑形象、展风貌、不辱使命”的标语,于是文艺队开始受罪了。
我和老祁分开每人一天陪着监督训练,不到天黑不准收工,我们只好干脆晚上睡到监狱里。齐林毕竟是请来的客人,监狱为此专门派了一辆专车接送他和效妍,他俩笑称车马费白领了,不下功夫都对不住监狱领导。
晚上的天气还是有些热,在院子里坐了会儿,贺明突然说:“不行去舞台上吧,那里好像凉快点。”
这些天监狱已尽可能让文艺队到舞台上合练,大多数时间,我都坐在观众席看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各自的节目。舞台对我而言很陌生,印象中还是很小的时候有过在上面合唱的经验。
木质地板发出咚咚的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响。尽管底下没有一个人,我还是有些发怵地停下脚步,左右看着距离,显得很新奇。
贺明已经像往常休息那样坐在舞台一角,双腿交错相盘,身体后倾,用手肘支撑在地上,微笑地看着我不太自然的神情。我们只开了旁边的侧灯,整个舞台泛着暗红的光亮。
“看什么看。”我朝他甩甩手,也在原地学他的样子坐下来。
“你知道你刚才的样子像什么?”
“什么?”
他咝咝地吸了口气,晃动着光光的脑袋,“就像我们第一次见你时,你和老祁站在教学楼外面时的样子。当时,我就想,哎,这个干部挺慈眉善目的,没见过!”
我撇撇嘴,“再夸。”
“真……的!”,他抬头望向天花板,“那时候我就觉得和你挺亲。你还记不记得听我说过去的、家里的事?你那么认真专心,我就想,这儿没人跟你一样会听我唠叨这些东西,真是好人。”
心里像涌进一丝蜜。我侧过脸继续望着他。我们隔着几乎半个舞台的距离,远远地抱着腿席地而坐,像这样说起过去似乎还是第一次。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在舞台中央空堂而过,清凉爽快。
此时的我们竟像多年的老友聊起过去的趣事,淡淡的喜悦、悠悠的思绪在夏夜里如那阵轻风飘来荡去,带走烦热与躁动。
聊了一阵,他忽然站起来,“闲着也闲着,让你检阅一下这两个月我们的成绩。”
说着,他将衣服解开在腰间打个结,跳到舞台后面高出的台阶上,站定了,冲我说:“给你做几个动作,看着啊。”
他伸展了双臂从身前划过一个圆圈,脚尖笔直地绷向前方,双腿跃起,从台阶跳下来,固定成一个展望的姿势,“这是渴望!”
紧接着他又旋转身体,双臂尽力伸向后方,整个身体几乎弯成一张弓的形状,“这是追索!齐林告诉我们要想象着前面有美女!你猜我想啥……你!”
见我咧开嘴笑了,他说:“注意了啊,接下来这个很重要,以后你可用得上了。”
只见他缓缓地渐次扬起双臂,左脚作为支撑,慢慢抬起右脚,然后双手自下而上像捧起什么东西,扬起的下巴伸下前方,“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唔,不知道。”
“猜猜……猜一下嘛。”
“喂……猪”,我大声喊。
他噘起嘴作了个猪的表情,“记着啊,只说一遍,这是‘我爱你’”
他拼命保持着阳刚而帅气的姿势,不时晃动一下,努力平衡身体,额头上一滴汗珠沿着脸颊滚落,停留在腮边莹莹闪着光。
爱有时很复杂,有时也很简单,有时很迂回,有时很直白,有时像行走于雾中难以捉摸,有时就像眼前这个男人的身姿一样直入心底。
门忽地被推开,一名巡逻队员探进脑袋,“这么晚还练习呢?”
“马上回、马上回。”沉浸在梦境中的我忙回答,贺明也忙穿好衣服跟在我身后。黑暗中,我摸索着抓到他的手,用指尖在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字。写一个,他就用头跟我碰一下,写一个,他就用头跟我碰一下,最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指。
原来爱可以这样说出口,爱可以这样被接受。
巡演就在夏末丝丝的微风中开始了。
除一辆大囚车外,监狱还派了辆小车让我、老祁、齐林和效妍乘坐。老祁觉着和年轻人挤在一块没什么可唠的,便自告奋勇去后面的囚车上陪武警战士。用他的话讲,这年头有不怕政府的,有不怕公安的,可没有不怕武警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安全!
我有些后悔,一直以为看押的武警不会同意我们上那辆车。







![高分泰腐剧《醉后爱上你》无删减中字13集观看下载[完结]-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5146188.jpg)

![[Waves][adonisjing]健硕体育生的巨兽写真书全见[120P]-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7/07211406183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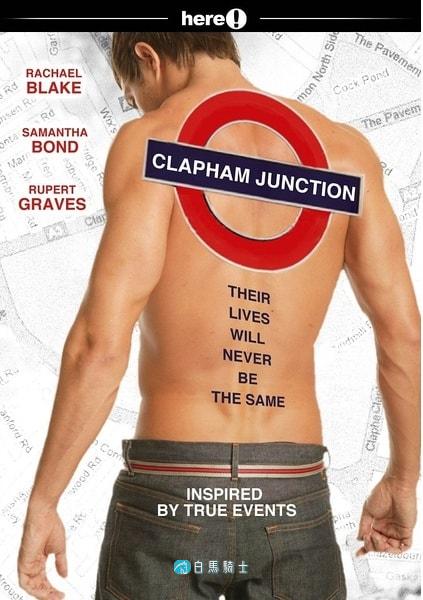

![[BLUEMEN]蓝男色NO.200 超人气体育男神允硕全见版-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3/1616077725.jpg)
![[1083张]惊人超大24cm,美混血帅哥网红李亚斯私照流出-白马骑士](https://www.bmqs.net/wp-content/uploads/2021/01/1632828731-092811321143.jpg)


- 最新
- 最热
只看作者